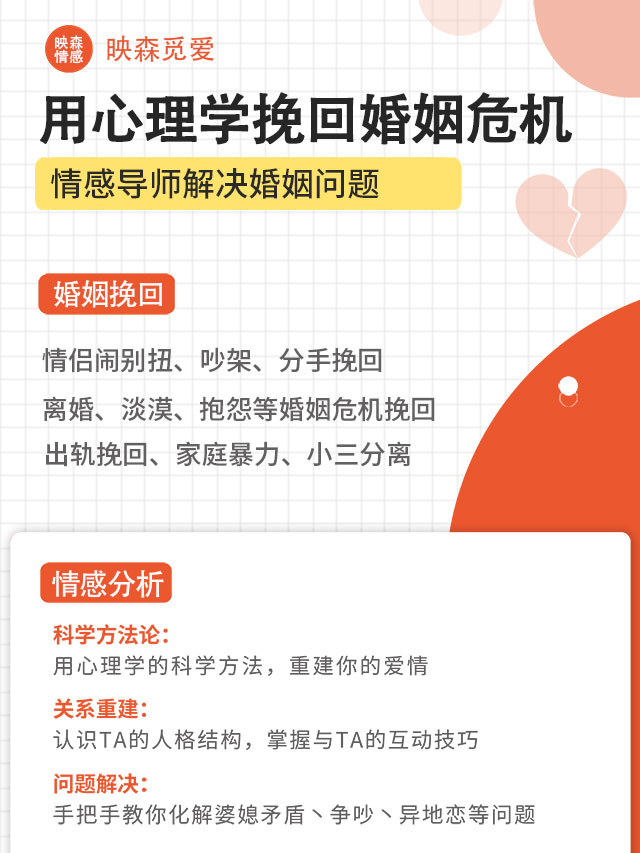【导语】李鸿章挽回利权?李鸿章 争议?有没有人知道,网友解答“李鸿章挽回利权”的简介如下:
情感目录一览:
- 1、清末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如何评价?
- 2、大臣谋国与生财之道:晚清上海的滩地清理运动
- 3、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遇刺,日方理亏,遂减少一亿两战败赔款
- 4、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创立是哪年创立?起到了什么作用?
清末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如何评价?
李鸿章,这是一个谈晚清历史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淮军和北洋水师创始人、“再造玄黄之人”等众多标签加身。但他更为人熟知和诟病的是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关系,《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李鸿章出面签的字,“弱国无外交”的酸楚在当时没有人比他体会的更深了。
1
要评价一个人就要结合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去看,用今天的标准去评价古人,“大圣人”也能挑出一身错。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拉开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或是因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或是因国家体量、武力强大,英法俄三国首先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争抢利益,三国利用武力胁迫、经济威胁等手段和实力不如自己的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说白了弱肉强食,实力不如人就要挨宰。
比如进入火器时代之后,硝石就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控制了硝石贸易不只能阻碍对手军备发展,更能获取暴利,而智利是唯一生产天然硝石的国家,英国依仗强大的海军逼迫智利签署不平等条约,控制了硝石的定价权。再比如都知道1775年至1783年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因为实力差距,双方签订的《巴黎和约》也称不上是平等条约,英国保留了大量经济特权,英国资本对于美国的剥削、影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结束。
2
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赞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这里面有些吹捧之嫌,但也是有感而发。
“铁血宰相”俾斯麦带领普鲁士王国,在19世纪中期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三场大战建立起了统一的德国,在这其中看似军事起了更大作用,实际上俾斯麦的外交手腕更重要。德意志地区处于中欧,处于英法俄三大列强包围之中,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到三国利益,俾斯麦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给普鲁士留出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一样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如向英国借“高利贷”,给俄国商品免关税,许诺给法国割地等等。只不过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轻松击败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统一的德国实力暴增,也成了列强,各种不平等条约自动解除了。
3
1853年黑船事件,日本国门被美国以炮舰打开,此后日本被逼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下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内外交困下,幕府统治被推翻,日本在伊藤博文等人领导下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大幕,为了发展,为了避免遭到列强组团压迫,日本可以说是使劲了浑身解数要抱上英国的大腿。伊藤博文等人贿赂英国官员、收买英国传媒、花高价买残次品拉拢英国工商界,宁可牺牲日本的短期利益,也要获得英国的认同、扶持。
比如1902年签署的《英日同盟条约》对日本来说是个不平等条约,日本义务太多,权力太少,完全沦为英国的“打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获得的利益大部分进了英国人的口袋,日本经济被英国资本操控直到一战结束。但这个条约是伊藤博文等日本领导人上杆子去签的,因为日本要发展、要扩张就会损害其他强国的利益,没有英国在背后撑着,日本早就被“围殴”了。
4
说白了后发国家想发展就要交“学费”,而在当时列强争霸的时代,这种“学费”往往是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存在,在国家实力不足以打破规则的时候,就要按着列强的规则来,俾斯麦、伊藤博文都是这么干的,李鸿章某种程度上来说做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事。李鸿章行事肯定有功有过,但在外交领域他确实是晚晴官员中做得更好的。
在李鸿章之前,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基本上处于没有交流的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之后也没啥变化,对于涉及西方的事务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直到列强的军队打上门才慌乱的派人去谈判。而在谈判过程中清朝官员也没什么技巧,要么强硬不懂变通,要么彻底跪舔,不了解国际局势,不懂得利用列强矛盾分化拉拢,就是硬谈,谈不拢接着打,直到清朝统治者被打怂了,不平等条约也就出来了。
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要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国家发展争取时间,比较典型的就是1874年的“马嘉理案”,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已经发出战争威胁,谈判趋于破裂,更终是李鸿章巧妙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清朝洋务运动30余年能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李鸿章是有功的。
其次李鸿章利用各国间的矛盾,改善了清朝孤立的外交局面,在谈判中减少损失。列强之间矛盾重重,清政府却对这些没有认知,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于各国列强的条件是全都答应,直到李鸿章主导外交工作才有讨价还价,利用列强间的关系减少损失。比如李鸿章人生更后一场和列强的谈判,签订《辛丑条约》,更早列强提出了瓜分中国、10亿两白银赔款等条件,几乎把清政府逼上绝路,是李鸿章利用列强在华利益上的冲突,分化瓦解八国联军,更终以不割地而平息事件,赔款降到了4.5亿两白银,这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更后李鸿章将清朝带入了国际外交体系中。清朝更早是“朝贡外交”,不主动和外国交流,一直当自己是“天朝上国”,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没啥改变,都是列强外交人员主动上门。直到1876年,在李鸿章建议下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大清才算是走进了国际外交体系中,打开了双方高层交流的渠道。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两国间的很多矛盾、冲突可以在初始阶段协商解决,不用等事情激化后走向战争。
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句话是很中肯的,李鸿章是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在外交谈判中有过受贿行为,但他并不是清政府中做出更终决定的人啊。比如使李鸿章备受诟病的1885年《中法新约》,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实际上是英国人赫德通过总理衙门以及自己在欧洲的关系绕过李鸿章主导了中法谈判,李鸿章根本插不上手,只是更终奉命去签个字罢了!
李鸿章的悲剧是作为臣子,他没能像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一样遇到锐意进取、雄心勃勃的君主,只能当一个“大清裱糊匠”;作为一个外交能手,他成为清朝统治者和列强眼中处理外交问题的唯一人选,仕途几起几落,却总被推到外交谈判的更前沿,在一份份耻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慈禧太后感叹:“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a
大臣谋国与生财之道:晚清上海的滩地清理运动
叶斌
19世纪末黄浦江苏州河口新涨滩地(绿色部分)
一
1895年夏天,《马关条约》初成,张之洞正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除了为清政府张罗赔款之外,还急着要偿还另外一笔债务。两年前他在湖北通过上海瑞记与地亚士两个洋行定购了四万零七百余锭纺纱机器,准备开办武昌南纱厂。后南纱厂招商失败,纱机存放上海。除了预付的定银2万余两外,购买纱机的货款由洋行垫付。此时这笔纱机欠款因为利息和汇率上涨等因素,累计已经达到60余万两,且还在增长中。
8月,张之洞派叶大庄到上海来开办烟土捐,想从鸦片贸易中开辟财源,收效甚微。适逢上海地价飞涨,冒名贩卖滩地的案件时有发生。在10月的一个案件中,3位地保联手将新闸50亩滩地冒名升科,准备以3万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洋行,不料那些滩地是有主的,事情败露。张之洞从这些案件中受到启发,于12月3日致电上海道台黄祖络:
闻紧连租界新堤地方有未升科地数百亩,为该处地保冒名禀请升科,业已零星转售。果有此事,该地保实属胆大可恶,应即澈底追究。闻此外未升科地甚多,该道务即督同上海县及叶丞一并切实查明,变价充公。此后如有禀请升科者,务必严斥,勿令朦混私占。
这封电报的重点,不在于追究冒名升科,而在于谕令未升科的滩地一律停止升科,“变价充公”。显然,张之洞在上海滩地中发现了新财源。
所谓“升科”,是指无主荒地晋升为科税田地。通过升科,国家获得田赋,而农户获得拥有土地的凭证。升科的时候,农户会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即升科银,一般要低于当时地价。1882年,上海县集中进行过一次滩地的清丈升科。当时的升科银是每亩6两,而上海道契反映的平均地价当时为每亩130两左右。滩地升科习惯上遵守“子母相生之例”,新涨滩地相当于毗连土地的延伸,只有毗连土地业主才有资格申请升科。
荒地升科政策是清政府鼓励垦荒的国策,升科政策的改变,以往都是由督抚奏请朝廷批准的。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为了平息民间为了争夺滩地沙洲的升科权而产生的冲突,奏准清廷禁止江苏滩地升科。不过这个政策早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又被两江总督怡良奏准废除了。张之洞暂时代理两江总督,未经奏准,一句话就把上海滩地升科之路堵死了,作风相当霸道。上海道台黄祖络对于张之洞惟命是从,接到来电后立即照办。12月8日,《申报》发布消息称,张之洞委托叶大庄在上海开办升科局。
张之洞像
二
叶大庄,字临恭,福建闽县人,1873年举人,*词人,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交好,此时正以候补同知身份担任张之洞幕僚。1896年2月,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离开江宁,回任湖广总督。行前,他给叶大庄安排了一个署理松江府海防同知的官职,让他继续在升科局办理清理滩地的差事。不过,叶大庄以一介微官,替张之洞在上海料理棘手事,实属不易。
3月28日,叶大庄与上海知县会衔发出告示,表示此次清理,是奉“署南洋大臣”张之洞的谕令进行的,目的在于将上海宝山两县的新涨滩地清理出来,“按照时值核实变价,拨凑要需”,以免它们被侵占盗卖,且此次清理的滩地,专指“无粮久荒官地”,即从未纳税、久未利用、尚未升科之地。
张之洞回到武昌之后,通过贩卖湘、鄂盐票筹得30万两,归还了一部分欠款。4月16日,叶大庄禀告张之洞,已经清出了约1000亩滩地,其中,宝山约300亩,上海约700亩。当时宝山那边充公的滩地,更低大约每亩100两,而上海浦东烂泥渡那边的地价,已涨到每亩1250两。以当时的进展推算,似乎余下的30万左右纱机债务,完全有可能通过卖地款筹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8月,叶大庄在升科局的差事被刘坤一免去。不久,又被免去署理海防同知一职。11月,江苏布政司任命他署理邳州知州。
对于叶大庄的去职,沪上中外媒体猜测与卖地款的账目有关。据《申报》8月30日报道,叶大庄曾经给刘坤一汇去10万两,得到的却是刘坤一充满疑问的批复:“此项滩地前据禀报清出约有八百余亩,此次据解银十万两,是否此项官地一齐售去,抑并未售完。……况上海地价昻贵,五六百圆起至四五千圆一亩不等,应明定价值。”可见叶大庄没有将清理滩地的账目与动态详细汇报,惹得刘坤一疑窦丛生,总觉他有所隐瞒。张之洞的人,刘坤一用起来不顺手,更终撤换了事。
叶大庄去职后,升科局一度由江海关委员曹荃生主持。曹两次到浦东勘丈滩地,觉得像是在抢东西。又看见有沿浦贫民祖传的滩地因为没有升科,要被充公,感觉伤心悖理,下不了手,便自己辞职了。
三
1896年12月,许宝书由刘坤一指派接办清丈局(即升科局)。许氏字阆轩,杭州人,江苏巡抚许乃钊的族孙,监生出身,咸丰年间投身兵营,曾因参与攻克被小刀会占领的青浦、上海县城而受到保举。1896年被委任为清丈局总办时已经69岁,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
许宝书清理滩地,采取挨户清查的方法,只要业主不能提供执业方单,或者丈量面积超出方单所载,不管是否滩地、是否纳粮,一律充公。例如,根据《申报》1897年9月6日报道,许宝书到二十五保五十图清丈的时候,对图内所有土地是否持有方单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绘制成图,将所有无单土地标注为红色,一律充公。上海居民将方单丢失或拿去抵押的情况本就不少,许氏超越权限,将他们的土地直接没收,可谓凶猛。又如,浦东杨家渡36亩滩地上密集居住着169户贫民,因受灾被前上海知县刘郇膏豁免钱粮,许宝书将他们的土地没收,卖给日商,令数百人无家可归。据《民国上海县续志》估计,许宝书圈屯的土地至少有三千亩。
在清理裕源纱厂土地的时候,为了迫使厂方补缴差额地价,许宝书申请动用官府力量,扣押裕源厂股东族人的盐票。不料裕源厂背后有李鸿章支持,后者于1898年5月致信刘坤一:
顷据上海裕源纱厂呈称,该厂地基共计七十九亩四分零,经升科局许守宝书丈量,有八十一亩二分零,仅多一亩有零,竟指为多至二十二亩有奇,每亩须另缴规银七百五十两,合计一万馀金,禀请在该股东同族朱瑞元淮岸盐票扣运作抵,向该厂缠扰,急须早为清结。……况当华商疲敝、洋商争利之时,直似助人排挤,于商务大局妨碍匪鲜。许守人本精明,而心计过于刻薄,弟所深知,办理升科局数年以来,万端搜求,声名殊劣,人言啧啧,想台端亦有所闻。兹据该厂详晰沥陈,弟系创议办理之人,自应据实代达。
李鸿章不仅指控许宝书捏造清丈数据,勒索钱财,更从政治高度指责他破坏旨在“挽回利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的指控当然是有分量的,1898年10月初,江苏布政司宣布许宝书署理淮安知府。
许宝书这么卖力地清丈土地,显然不仅是为了替张之洞还款,还款只是他搜刮土地财富的借口。许宝书的行动需要多方支持配合,其收益也令多方获利。参与这场饕餮盛宴的,既有从刘坤一到许宝书的官僚群体,也有衙役、地保、掮客等各类角色。
四
清丈局对于上海土地财富的搜刮激起了上海本地人的抗议。抗议的声音首先来自上海的报纸。《新闻报》1898年9月18日的社论《论涨滩充公之可骇》,揭露了许宝书通过变卖充公土地牟利的途径,即先把充公土地贱卖给自己人,再由后者抬价出售。实际上,许宝书的弟弟许韬安,就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地贩。
上海本地的士绅阶层一直不敢对于清丈滩地的行动表示意见,许宝书的离任让他们觉得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开始松动。为了防止继任者继续搜刮,1899年7月26日,杨德鑅等15名上海本地绅士联名给上海道台、松江知府和上海县令呈递了一份禀帖,请求“凡完粮业田,有印串可凭、印册可证者,概免充公”。这样的请求,十分卑微。而上海道台却在批复中表示,升科局由两江总督设置,他无权代为决定。
15名上海绅士倔强了一回,于9月14日再次呈禀,请求对于有粮(有纳税记录)无单(无执业凭证)之田,由上海县补办执业凭证,不令充公。9月23日,上海道台批示称,已经请示过两江总督,“沿江地亩分别有主无主,以顺舆情”。这个批示虽然对于上海绅士的请求作出了让步,不过回避了禀帖中含义明确的用词“有粮无粮”、“有单无单”,代之以含义不明确的“有主无主”,从而留下了下一步的寻租空间。
杨德鑅等15名联名具禀者都是在官僚系统中具有一定地位而离职在家的绅士。如杨德鑅和李曾珂都是进士、县令,姚文枏和葛士清都是举人,张焕纶是廪贡生、候选同知。这些本地绅士的官阶都比较低,在高官众多的上海,他们的影响力有限,没有能够及时制止清丈滩地的行动。作为上海民意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及时的反馈,但是结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除了报纸评论和绅士请愿之外,上海的抗议还有第三个渠道,御史的弹劾。10月8日《申报》登载了一份御史奏折,指责许宝书利用清丈滩地的机会,“将有粮田亩变价充公”,所得款项去向不明。御史名叫宋承庠,松江华亭人。他有个朋友在《申报》任撰述,《申报》因此得到了这份奏稿。
朝廷收到这份奏折后,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查明具奏。1900年1月16日,刘坤一复奏称,纱机欠款更后已经增加到了近88万两,滩地变价所得不到25万两,张之洞提供了约35万两,不足部分是他从其他渠道筹措填补的。意思很明显,清理滩地是在为张之洞善后。至于许宝书,刘坤一只是为他认领了一个小错误,说是有一块地属于“一业两主单串各执”,即执业凭证和纳税凭证有两个业主各自持有,许宝书所派办事员误将该地充公,许有失察之责。这件事牵涉到张之洞、刘坤一两大权臣,清廷不欲深究,更后给了许宝书一个“交部察议”的更轻处罚了事。
刘坤一竭力为许宝书辩护,表面上没有作出什么让步,实际上还是有所收敛。自宋承庠上奏以后,清丈行动即陷于停顿,清丈局后续工作主要是继续变卖原来囤积的充公地,直到1908年并入会丈局。但经此一役,上海涨滩的升科之路也被彻底堵死。
张之洞1893年所购四万零七百余锭纱机因计划不周、财力不足等原因,多花了很多冤枉钱。好在这批纱机后来作价50万两官本,被张謇的大生纱厂分批认领,总算物尽其用,为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滩地新政标志着国家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和买卖,主动从城市土地的财富积累中汲取财政资源。这场滩地清理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土地的城市化,并促使农业时代的滩地升科制度走向崩溃。同期上海道契有一个申领高潮,与此不无关系。
这场滩地清理运动促进了上海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上海人对于这次对上海土地财富的掠夺一直耿耿于怀,姚文枏主纂的《民国上海县续志》对此深表不满。在清末上海自治运动中,主事者也一直在争取把滩地收入转化为城市自治基金。
校对:徐亦嘉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遇刺,日方理亏,遂减少一亿两战败赔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17日),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日子。这天也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此前,日军将大清的北洋舰队击败,北洋海军的舰船或被击沉或被俘获,甲午之战以大清国失败而告终。日本政府声称: 清国必须选派议和大臣,该议和大臣须有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商让土地及与日本办理交涉能签字画押之全权 。慈禧太后因清军海陆皆败,更是求和心切,得知日本人的要求后便一人做主,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
1895年4月17日,马关春帆楼,清国的全权大使李鸿章、日本的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画押,据说这条约是比当年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江宁条约》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可就是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屈辱条约的签订,也是极其来之不易的,甚至是中方全权代表李鸿章耗费了自己的鲜血才换来的。这事说起来是何等荒唐可笑,但又是千真万确的,是 历史 上真正发生过的真实情由。
早在头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之战)清国落败以后,慈禧下懿旨钦定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时,李鸿章早已明白战败国无外交的事实,情知被别人打败了求和不会有好结果,但在慈禧的一再催促下,不得不动身前往日本。
日方的全权大使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他俩已经在马关(今日本本州山口县下关市)恭候多日了。
李鸿章在来日的海船上,屡屡接到清军连连败退的战报,日军不仅团灭他费尽心力组建的北洋水师,还在陆战中所向披靡,从朝鲜半岛一直打到中国东北,已经占据营口,南面的日军攻占了澎湖列岛,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夹击之势,大清已处于绝对劣势之中。因此,李鸿章一到马关,见到伊藤和陆奥,便立即提出要日本方面停战的要求。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早已甩脱对大清的更后一丝敬畏,有恃无恐,坚决不允停战,而是要先签和约,再谈停战。
李鸿章放低姿态,再三请求,伊藤才提出停战条件,一上来就要大清将山海关、大沽口 、天津作为抵押品抵给日本,日方才会准许停战。日方所提条件原文(译文):
李鸿章一听,这哪行?这三处皆是京畿要地,倘若抵押给日本,岂不是引狼入室吗?左思右想,无奈先把停战谈判暂且搁置一旁,先商议和约条款细则。
伊藤、陆奥都是狡黠精明的厉害政客,看着清国外强中干,全权议和大臣亦很懦弱,遂肆无忌惮地提出了让人根本无法接受的苛刻和约条款,还当面轻慢、戏辱李鸿章。在国内位高权重、颐指气使惯了的李中堂因处于弱国地位,既不能反唇相讥,又不能拂衣而去,更不能俯首听命,于是便玩起了中国人更擅长的拖延之术。
拖延术李鸿章驾轻就熟,惯常使用,今天说身体不舒服明天再议,明天说天气不好后天再议,后天说吃坏了肚子大后天再谈,总之是一拖二延三不理,双方的谈判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可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有若无。
李鸿章的拖延伎俩,伊藤博文岂能看不出?在他的一再催逼下,李鸿章无奈再次回到谈判桌上。伊藤故意告诉李鸿章,日军攻占澎湖后正向台湾进军。李鸿章早就知道日本有吞并台湾的企图,但突闻此话,仍然惊出一身冷汗。他强作镇定说:“ 几日前议及停战,贵大臣不肯应允,是为出兵台湾之故吗 ” ?
伊藤笑答:“ 绝非如此 ”。李鸿章无奈中搬出大英帝国做挡箭牌,说:“ 贵国倘占台湾,英国岂会甘心,必不答应,如之奈何 ”?
伊藤:“ 英国固守局外中立,无任何出兵干涉之理由 ”。
李鸿章争辩道:“ 除我国之外,英国不欲他国盘踞台湾 ”。
伊藤微笑道:“ 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的任何一地,我欲割取之, 哪个国家能 (敢) 出面抗拒 ”?
战场上输掉的,谈判桌上绝对赢不回来。日方终于以苛刻的条件迫使清方撤回停战协议,达到了一边打一边谈的目的。
李鸿章代表清廷提出的停战要求被伊藤首相拒绝后,日本举国欢腾,主战舆论更是高涨,占据了绝对舆情优势。据记载,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在头版登载了*诗人山田松堂的一首诗:
日本朝野主战气焰高涨,主和派失去了话语权,受此影响,关东平原西北部的群马县有一个叫小岛丰太郎的浪人(无业游民),认为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是暗中挑衅日本的幕后主持,遂决意铤而走险,寻机行刺李鸿章。
日清第三次谈判那天,小岛暗藏手枪躲在马关外滨町邮局前街道拐角处,待李鸿章谈判结束后乘轿子返回住处引接寺 ,在争相围观的人群中穿行路经此处时,便直奔轿子前,用手按在前边轿夫的肩膀上,趁其惊愕愣神之际,拔枪对准轿内的李鸿章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李的左眼下方的颧骨处,再往上一点就是左脑,确实很险 。李鸿章毕竟是戎马一生、久经沙场的老将,中弹后,他立即以手按住伤口止血,强忍剧痛命轿夫抬轿速速离开,坚持到引接寺旅馆门口下轿,神情自若地在左右的扶持下走了进去。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政府也很紧张,同时有些狼狈。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尤其害怕李鸿章借此机会回国,谈判中断,更担心西方列强趁机介入并干涉。他俩一面催促山口地方法院尽快审判刺客小岛丰太郎,一面亲自到引接寺旅馆探视李鸿章的伤情,致歉并慰问。睦仁天皇也下旨严惩凶手,以保国家声誉;他还特地派侍从武官携带两位御医和12名护士前往马关为李疗伤侍养。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迅速传遍欧美,列国报刊上连篇累牍,都斥责日方无理,和谈不成,何必采用暗杀的肮脏下作手段?西方报刊向来直奔主题,不讲情面,大有共同讨伐日本之势。
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见伊藤、陆奥两大佬亲自前来道歉,立即要求日方马上停战。伊藤、陆奥立马答应。接着李鸿章裹伤与日方继续谈判,议定和谈条款,日方不愿多做让步,只答应减免一些战争赔款,李鸿章也别无他法,这便有了《马关条约》的11条和款,大约为以下6个方面:
日本政府原本准备向清国索赔军费3万万(亿)两白银。因大清特使李鸿章被小岛丰太郎谋刺,挨了一枪,为挽回不利的国际声誉,同时为安抚列强、安慰李鸿章,更终同意少要1亿两战争赔款,只索要2亿两白银 。李鸿章挨了一枪,差点丢了性命,更终为大清省了1亿两白银的赔款,事后他对左右自嘲道:“这一枪没白挨啊,一颗子弹、一捧鲜血换少赔1亿两银子,很值 ” !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让李鸿章个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更是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空前的民族危机,使本就积贫积弱的清国更加衰弊,因而激起了国内有识之士及世界各地公正舆论的普遍声讨与激烈反对。
【插图源自网络】
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创立是哪年创立?起到了什么作用?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 招商局。
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 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等等。这使洋务派意识到必须是 “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 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派沙船 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洋泾滨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 。
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成立时有轮船6艘,
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开办后由于亏损严重,朱其昂被迫辞职。次年7 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18 76年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以222万两银子买进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及其码头、仓库等财产,
招商局初具规模。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 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更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招商局成立后,在 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 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 为盈。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 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 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 利。
【回顾】李鸿章挽回利权?李鸿章 争议?看完不再为情所困,更多关于“李鸿章 争议”的问题关注映森:https://www.zshdch.com/